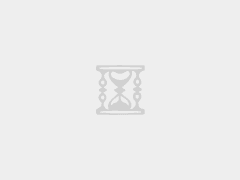肖燕翼先生《古书画名家名作辨伪三十例》(以下简称《辨伪》)经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已于年前面市。作为文博系统专家摒弃门户之见,直言馆藏作品真伪,而打假古书画作为一种天然“正义”,更加讨好,《辨伪》一度广受好评。
但此前已见吴斌、林霄等学者对先生《燕肃《春山图》辨伪》、《宋克书陶诗并画竹石小景两本辨伪》、《祝允明書法偽作的再發現》等论文较为武断的鉴定考证方法和结论提出商榷。《辨伪》一书涉及赵孟頫、邓文原、俞和等名下多件作品,恰好是笔者研究方向,关注之余,同样发现书中图像分析简略,文史考证也较粗疏,又涉及到古书画鉴定的方法与逻辑等原则性问题,恐引误从,再作辨析,以为读者兼听。
文史考证
张珩在《怎样鉴定书画》(文物出版社1966年版)中提出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是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而印章、纸绢、题跋、收藏印、著录、装潢等作为“辅助依据”,这是现代鉴定学的开端,也是要求。
关于文史考证在古书画鉴定中的地位问题,张珩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既未纳入“主要依据”,也未纳入“辅助依据”,而是以“比较密切的几方面”来叙述。
笔者认为,文史考证与“辅助依据”一样,不应作为鉴定的起点,而应作为鉴定之后的检验环节。具备丰富经验的鉴定者,总是勇于“闭卷考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准确鉴定,并在后期不断获得辅助证据和文史考证的检验。
以图像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古书画鉴定,门槛较高,要讲究科学性,需要一些原则和技术,可能比较枯燥,并且风险较高。
于是,实际鉴定操作中,文史考证往往作为缺乏鉴定经验者寻找“破绽”“硬伤”和“铁证”的捷径来使用,凌驾于“主要依据”之前,甚至回避对“主要依据”的分析。而“破绽”不破、“硬伤”不硬、“铁证”不铁,则是近年来古书画鉴定领域多次草率的真伪争议的主要原因。
照顾到读者对“破绽”“硬伤”“铁证”的偏爱,以及《辨伪》一书的类似倾向,本文将文史考证作为第一部分,而包括图像鉴定科学性的一些原则,以及本文提到作品的鉴定问题,都放在最后一个部分。
古代文史资料流传下来,陷阱一点不比古书画作伪少,文史考证同样有其原则,史料本身首先要辨真伪、寻来源、明省简,避免孤证、避免道听途说。
《辨伪》一书中的很多文章和章节,正是违背了以上原则,大量使用孤证和二手甚至三、四手材料作为立论起点,然后附会论证,“罗织”特征非常明显。
一、《赵孟頫〈自画像〉〈饮马图〉辨伪》(p91~101)之辨析
关于赵孟頫《自写小像》(图1),《辨伪》的考据主要有两点:
1)、“其‘破绽’主要出在明宋濂所书《赵文敏公小像赞》一文中”。宋濂有跋“公之外孙吴兴林子山”,关于“林子山”到底是赵孟頫外甥还是外孙问题,作者唯一采信的史料是清代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二》的转述:“《石田集》有题林子山《濯足图》注云:‘子山,赵文敏之甥,有隐操’”,由此认定《自写小像》以甥为孙的“破绽”,并断言“对宋濂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2)、宋濂在题跋中将赵孟頫“大德己亥”四十六岁误作四十七岁,又将赵孟頫卒年“至治壬戌”误作“至治辛酉”,《辨伪》认为“宋濂当然不会将赵孟頫的生卒年搞错”。
图1 赵孟頫 自写小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外甥还是外孙
以三、四手的孤证,作为考证出发点,奢谈“绝对”,其危险不言而喻。
林子山其人文献累牍,不难查证,台湾学者王德毅等人继1972至1976年《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后,1979年至1982年又编纂了《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作为宋元史学及艺术史研究的入门必备,“林子山”词条出现在元人卷第677页,计有《宋文宪公全集》等书目7卷、文献8笔(图2)。
图2 《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书影
书目中宋文宪公即宋濂,宋濂为林子山写了两篇文章《玄武石记》《愚斋集序》,显示二人过从之密。愚斋,为林子山的斋号。据宋序:“(林子山)髫龄之时,即解缀篇章,有外氏赵文敏公家法”,这里“外氏”即“外祖父”,毫无疑问。
李铸晋据以在《鹊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一书中为林子山立小传:
“林静,字子山,号愚斋,孟頫外孙。曾祖弁,祖友信,父德骥,皆为武职,管军总管,俱读书知文。静髻龄时,即解缀篇什,有外祖赵文敏家法。研穷经史百氏,虽老释玄诠秘典,悉掇其芳润。从金华宋濂游,为诸生。郡县累辟不就,著《愚斋集》,宋濂为之序,亦能图画。(见《宋学士文集》、《张光弼集》、《苏平仲集》及成化《湖州府志》。)”
当然《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仅仅收录了与传记有关的部分文章,以简单主题词“林子山”粗略检索《四库全书》,得书25卷,文献34笔,剔除无关和重复亦超过20笔,涉及林子山与赵孟頫甥、孙关系的计有3笔:
1)、陶宗仪《南村诗集》卷四《題林子山画次韵》有注:“子山乃松雪外孙,余家有其画”;
2)、凌云翰《柘轩集》卷二《草心轩为林子山赋》有注:“子山舅赵仲穆为画荤草,因以名轩”;
3)、张丑《清河书画舫》著录沈周題林子山《濯足圖》与《石田集》略同:“林子山,赵文敏公甥,有隐操”。
陶宗仪、凌云翰、宋濂等,与林子山直接交往、背靠背独立著录、反复著录,其权威性显然远高于明朝中后期道听途说的沈周和张丑,更高于抄录转述的顾文彬。
2、甥、孙之误是如何产生的?
将外孙作外甥的事情,最著名的公案莫过于王蒙,从元末开始就已经混乱,《草堂雅集》卷十二:“王蒙,字叔明,赵文敏公之甥”;《图绘宝鉴》卷五:“王蒙,字叔明,吴兴人,赵孟頫甥”。
这个问题明人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已经解决:“赵孟頫,字子昂……长子雍,字仲穆。婿王筠庵国器,字德琏,则王蒙叔明父也。”
1930年1月,翁同文在《大陆杂志》26 卷1 期发表专文《王蒙为赵孟頫外孙考》,成为今天赵孟頫世系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
王蒙题跋赵孟頫《兰亭十六跋》(图3,赵书由十六跋拆为十三跋,又经火烧为残本今存东京国立博物馆,王蒙跋拆出后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考《中华书画家》2015年7期,田振宇《赵孟頫跋〈吴静心本定武兰亭〉辨伪》)称赵孟頫为“先外祖”则是实物证据。
王蒙还有一帖《致德常判府厚爱帖》(图4)称林子山为友人:“友人林静子山,吴兴人,亦赵氏之甥也”,这里的赵氏是谁呢?
图3 王蒙跋赵孟頫《兰亭十六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用反证法,假设赵氏为赵孟頫,则林子山比王蒙长一辈,王蒙不可能称长辈为“友人”并向他人举荐,同时也不会唐突地将“先外祖”简称为“赵氏”,所以前面的假设是错误的,林子山只能与王蒙同辈。同时,句中“亦”字也可间接补证,需要王蒙是赵氏之甥,林子山“亦赵氏之甥”的“亦”字才有着落,这里的赵氏只能是赵雍或赵奕,这个结论与凌云翰“子山舅赵仲穆”的著录完全一致。
由此,又可推测沈周等人对于林子山的错误注释很可能来自于类似语焉不详的“赵氏之甥”的误解。
大量的文献证据表明,林子山不是“赵文敏之甥”而是“赵文敏公之外孙”,宋濂题跋是正确的,反而《辨伪》一文对于所提出的最重要“破绽”,完全未进行最基础的文献检索和辨析,偏信偶然性阅读,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图4王蒙爱厚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是亲外孙还是攀附外孙?
针对“外孙”问题,《辨伪》又引用“有关研究”推理论证:
“有关研究揭示,按六女长幼为序,前五女分别嫁与强文实、费雄、李元孟、王国器及刘姓一人。其第六女,一说早卒未婚,一说嫁与韩姓某人。总之,赵孟頫的女婿中未见有林姓之人,林子山当然不会是赵孟頫的外孙。”
引用“有关研究”当然是可以的,但有一定规范和技巧。本例中“一说嫁与韩姓某人”与“一说早卒未婚”强烈胡否,必有一错的情况下,本应追溯史源,再判断甚至再研究,作出说明,这是规范问题;通过研究,不难发现个中原因,这又是技巧问题。可惜《辨伪》罗织“证据”心切,无论对错,不作任何说明,两条都用,轻易就放过了解决矛盾的宝贵机会,后面的“林子山当然不会是赵孟頫的外孙”就只能是想出来的当然,不是必然。
实际上,这个第六女就是早卒未婚,时间是至大二年正月廿日,原因是大德十一年江浙大饥荒引起的至大元年的江浙大疫(可参考《书法研究》2016年第2期,拙文《赵孟頫告病闲居时期所作书法考》,亦可参考即将出版的拙著《赵孟頫闲居考》),赵孟頫有三件书信专门说幼女夭亡的事情,分别是:
1)、上海博物馆藏,致静心相干《小女帖》:“小女不幸弃世”;
2)、日本静嘉堂文库藏,致中峰和尚六札册《幼女夭亡帖》:“正月廿日幼女夭亡”;
3)、日本静嘉堂文库藏,致中峰和尚六札册《亡女帖》:“亡女蒙吾师资荐,决定往生”。
所以赵孟頫第六女既不可能嫁与林子山,也不可能“嫁与韩姓某人”。
那么“嫁与韩姓某人”的错误研究是怎么来的呢?沈梦麟《花谿集》卷二记载:“会稽儒者韩征君(介玉),渠是魏国赵公之外孙”,既然是外孙,那么“一定”是赵孟頫女儿的儿子,前五个没有姓韩的,就安排给第六女。原来这个二手材料也是用孤证来安排的。
《花溪集》里记载赵孟頫的韩姓外孙是不是伪史呢?当然不是,没有第六女“嫁与韩姓某人”,韩介玉照样可以是“魏国赵公之外孙”,就像儿子并非亲生的才叫儿子一样,并非一定要赵孟頫的亲生女儿的亲生儿子才叫外孙。没有第六女“嫁与林姓某人”,林子山照样可以是“魏国赵公之外孙”。
大德二年、三年,受到皇太后伯蓝也怯赤提携(参考《书法》2019年3期拙文《赵孟頫隆福写经考》),赵孟頫先后举荐写经、出任江浙儒学提举,成为江南士人入仕的重要通道,戴表元在《紫芝亭记》中称颂“天下士被其欬唾者,嘘为祥风;饮其膏沐者,润为荣河”。在取消科举的大环境下,缺少仕进通道的江南士人,对于能够举士入官的赵孟頫无不争相攀附。赵孟頫的血亲和姻亲关系以及非血亲姻亲关系中,有很大一部分牵连攀附关系,由远攀近,由无攀有。
查《松雪斋文集》卷八《先侍郎阡表》,赵孟頫之姊赵孟家适会稽韩巽父,韩介玉当为韩巽父的孙辈(也不一定是嫡孙),无论如何算也不是赵孟頫的亲外孙,最多是外侄孙,这就是由远攀近。
又如,唐门岳家,“赵文敏公,至与之婚姻”实为与赵孟頫某个侄辈或侄孙辈婚姻;德辅教授由一般友谊关系的“仁弟”变成有辈分论序的“仁侄”;赵孟頫致季宗元称“总管相公尊亲家”实际上是上面不知哪一辈有过姻亲关系“世附女萝”,等等。
林子山与赵孟頫的具体亲缘关系尚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不是亲外孙,而只是攀附外孙。
4、宋濂题跋中的时间误差
宋濂题跋中赵孟頫的年龄和生卒两次出现错误,这是事实。但《辨伪》认为“宋濂当然不会将赵孟頫的生卒年搞错”则未必当然。
实际上,赵孟頫自己记载自己的年龄都不能保证绝对准确,如五十八岁时的《长儿长往帖》自述年龄为“六十之年”(图5)。
图5 赵孟頫五十八岁作品《长儿长往帖》自称六十之年
1)、饱受诟病的《元史》与宋濂的“前科”
宋濂又是否“当然”不会将赵孟頫生卒年搞错呢,先要说一说《元史》的编纂问题。
洪武元年(1268),朱元璋一登基就下诏催修《元史》。这次修史,从洪武二年(1369)二月初一正式开局,到秋八月十一日结束,仅用了188 天,便完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列传63卷,共159卷。
由于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到七月初一,共143天,增顺帝纪10卷,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下卷,列传36卷,共计53卷。
合前后二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210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共188万字。
由于编写仓促,《元史》备受后世史家诟病,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元史》中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错误百出;清代汪辉祖的《元史本证》即指出《元史》中3700余项错误。
仅以《赵孟頫传》为例,把赵孟頫五兄赵孟頖“以父荫补官”之事张冠李戴到赵孟頫身上,妄改“注官”为“调官”等,都极不严谨。
显然,不可以由大量错误而推断《元史》是后世伪造。
两次纂修,历时仅331天,参与纂修者共19人,宋濂即总裁之一,出现点时间误差再正常不过了。
2)、宋濂出现多重时间误差的性质
研究一个古人的时候,对于年号、年龄、干支、公元不可能逐年背诵,而是通过选择性记忆关键节点结合数学计算,只要记住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阴历丁酉、赵孟頫四十四岁、世寿六十九岁,即可推算大德年间任何一年的对应值、赵孟頫的生卒年、任意年龄对应的干支或任意干支对应的年龄。正常情形下,宋濂整个题跋过程使用的正是这样的方法。
但是选择性记忆加数学推演的办法缺陷也很明显,如果初始数据错误,后续推算就会出现系统性错误,一错全错,宋濂第一步把“大德己亥”错配到赵孟頫四十七岁,就必然导致正确掐算下六十九岁为辛酉:69-47=22=辛酉-己亥。
另外,《辨伪》还忽略了赵孟頫至治壬戌(1322)到洪武八年(1375)乙卯,本应1375-1322+1=54年(古代纪年除年龄用虚岁外,一般度过年也虚加一年,如赵孟頫《玄庙观重修三清殿记》、《红衣西域僧图》、《先侍郎阡表》、《濮君墓志铭》、《灵隐大川济禅师塔铭》等均是如此计算),而非55年的“破绽”,这个破绽同样是由于初始数据错误引起的全面错误,乙卯-辛酉+1正好等于55年。又或宋濂由错误的55年往前倒算,得到同样错误的至治辛酉和大德己亥四十七岁。
而实体的文献、年表或数据库的手工查阅比记忆计算法就相对安全得多,即使出错往往也只是孤立错误,这正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总的说来,宋濂题跋中,林子山与赵孟頫“亲缘”关系的内容相对隐秘,在赵孟頫年龄记忆上出现了一个是人就会出现的正常错误,导致了另外两次正常掐算下的系统错误,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题跋。
5、其他
关于《自写小像》本幅的问题,款印皆伪,但原作有明显裁切痕迹,原作应为《谢幼舆丘壑图》一类的长卷,拆改后的补款补印应予无视。从绘画水平和风格要素看仍应为赵孟頫学唐法,是后世所没有的。
《自写小像》的绘制背景,涉及大德二年提调写经前后,在龟溪上游营建隐居的选址、写生、邀访问题,相关作品有《谢幼舆丘壑图》《幽篁戴胜图》《致民瞻十札卷•不闻动静札》《致民瞻十札卷•便过德清札》《致费拱辰·舟从枉顾帖》《陋室铭》《致赵孟頔·违远帖》等书画作品、以及大量相关诗文,这里植入一个硬广,欢迎关注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史·事实与视角》丛书,拙著《赵孟頫闲居考》(图6)中“告罪闲居”一节将专门解读。
图6 拙著《赵孟頫闲居考》(封面设计为临时稿)
《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辨伪》(p137~145)之辨析
章草对于邓文原来说是孤品,但题款26字是小楷(图7),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芳草帖页》《跋周密藏保母砖卷》等参考品,以及印鉴作为辅助证据可核对,同纸元人题跋俱真迹无疑。
图7 邓文原 章草急就章(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但《辨伪》认为该卷为伪迹。其主要依据是邓文原的签款“大德三年三月十日……书于大都庆寿寺僧房”,而“据《元史·邓文原传》记:‘大德二年调崇德教授,五年,擢应奉翰林文字’”,由此结论,邓文原大德三年人在江南,不可能笔在大都写《急就章》。
当然这里用的又是孤证证伪。
1、追溯史源
正史中人物传记,主要取材于“行状”“神道碑”等,改写时,为了避免直接抄袭,造句遣词往往要换同义词或近义词。
《元史·邓文原传》来自吴澄为邓文原写的神道碑《元故中奉大夫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邓公神道碑》,见《吴文正集》卷六十四,原句为:“大徳戊戌,部注崇徳州教授”,《元史》把“大德戊戌”换成同义词“大德二年”没有问题,但是包括《赵孟頫传》《邓文原传》在内,都把“注官”换成“调官”,意思就完全变了。
2、注官与守阙
《元史》卷八十三《选举三》:
“凡注官守阙:至元八年,议:‘已除官员,无问月日远近,许准守阙外,未奏未注者,许注六月满阙,六月以上不得预注。’二十二年,诏:‘员多阙少,守阙一年,年月满者照阙注授,余无阙者令候一年。’大德元年,以员多阙少,宜注二年。”
今天的公务员考试是定额招考,考中就上班。古代不能跟今天比,古代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国初往往缺人,举荐、注官、调官可以说是一回事,承平时期要维护基层政权稳定,就不可能等阙官了再招,需要有适度的“冗官”注籍在册,随时听用,宋代通过吏部铨试试中注册,如赵孟頫“未冠,试中国子监,注真州司户参军”,元代恢复科举以前人才选拔主要靠举荐,比如赵孟頫被程钜夫举荐入仕、自己又举荐邓文原等人写经改授官职,被举荐者也是先注册听用再调官赴任。
制度性冗官到朝代中后期普遍造成冗官过滥的问题。比如赵孟頫注官听用的南宋后期,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臣僚上言:
“即今吏部参注之籍,文臣选人、武臣小使臣校尉以下,不下二万七千余员,大率三四人共注一阙,宜其胶滞壅积而不可行。乞命吏部录参、司理、司法、令、丞、监当酒官,于元展限之上更展半年。”(《宋史》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四》)
三四人共注一阙,每人任期三年,排队就得排上9~12年,所以赵孟頫在南宋末年考上注册公务员只能在家听用,再加上未到年龄,根本没有调官上任的可能性。
除了铨试、举荐注官,届满、假满离任官员也在排队听用行列。赵孟頫在元代还有一次候阙记录,大德十年秋,赵孟頫以“疡发于鬓”辞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亦请关注拙著《赵孟頫闲居考》“告病辞官”一节),据欧阳玄《赵文敏公神道碑》:“以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除扬州路泰州尹,进阶中顺大夫,需次于家”,神道碑省略了辞官情节,也不注年月,《元史》则只言“未上”,但这都不算错误文献。只是遇到这样的传记,孤证立论削足适履就很危险了。通过史源追溯,知道了“未上”的原因是“需次”。
笔者所见最早使用“需次”一词为宋朝,指官吏授职后,按照资历依次补缺。
元祐初,上官均上言:“诸路吏选,有待试,有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文献通考》卷三十八《选举考十一》);
实例如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的尤袤“注江阴学官,需次七年”,果然需次了7年(《宋史》卷三百八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又如,南宋楼钥有诗:“九江需次今几年,去去渌水依红莲”,需次无期(楼钥《攻媿集》卷四《送袁恭安赴江州节推》);
元朝后期,需次甚至有长达10年的,如王豫齐曾两次需次:“泰定四年(1327)郡守论荐公于淛东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署台州路临海县儒学教谕,需次,至元三年(1337)始就职……至正元年(1341)调谕天台,需次七年乃视学事”,两次合计需次17年(谢肃《密菴文藳》壬卷《故庆元路儒学正豫齐先生王公墓志铭》);
赵孟頫从至大二年需次到至大三年,如果不是被元仁宗召入东宫,恐怕也会有“泰州需次今几年”的问题。
3、邓文原何时赴任?
那么邓文原大德二年受赵孟頫荐举赴大都写金字藏经而注官崇德,要需次到什么时候呢?
邓文原《巴西文集》第一卷、第一页、第一篇文章、第一行:“崇德,古御儿地,大德己亥,吾尝为其州文学椽”(图8),己亥也就是大德三年,非常幸运只需次了1年左右。
图8 邓文原《巴西文集》书影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明抄本
干支纪年不比数字“二、三”存在抄错、污损、涂改、添笔问题,非常准确,而一本书最难出错的就是卷首第一行。
如果还不放心,可再看同卷第二篇文章:“大徳己亥,余职教御溪”,仍然是干支纪年。
按经史子集顺序,《元史》是必备书,《巴西文集》则相对罕见,要造假,也未必知道邓文原大德三年前半段在大都需次。
出现矛盾的人物传记与规章制度,二者都来自《元史》记录,该信哪个?这就需要权衡史源亲疏,解决逻辑矛盾,增加更多第三方独立无关联关系的史源信息,不能轻易用未经辨验的孤证否定重要古迹,尤其还在鉴定者对“主要依据”认识不清的情况下。
《赵孟頫〈小楷书道德经卷〉辨伪》(p103~109)之辨析
关于赵孟頫小楷《道德经》的“硬伤”。经考证,延祐三年赵孟頫在大都不在湖州,而小楷《道德经》(图9)年款为“延祐三年”地址却是湖州德清的“松雪斋”,“身在大都为官的赵孟頫,怎可能在松雪斋为人书写《道德经》,此为考据上的‘硬伤’,《道德经》必非真迹”。
《辨伪》又把重要篇幅集中在“两日书成五千字”这样的“破绽”上,以一己之经验认定赵孟頫两天写不出小楷五千字:“该卷长618.6厘米,若将这六米多长的小楷书手写卷两天内写完,大概只能令观者叹为神技了”,甚至罗织杨载延祐七年题跋赵孟頫《黄庭经》:“松雪翁年老不复为人作小楷书”推论赵孟頫“至晚年放出话,从此不写小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文末并将《道德经》与《六体千字文》归类,再次将作伪者指向陆士仁。
图9 俞和作伪赵孟頫款 道德经(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从署款中斋号的使用看主、辅助依据的应用
一址一名,针对赵孟頫这个个案来说问题不算太大,但并不保险,像张大千一样走到哪里书房都叫“大风堂”的书画家并不鲜见,如果赵孟頫也偶有此习,或者一时抄誊笔误呢?
我在研究俞和作伪赵孟頫书画时也注意到这一条,但并没有作为主要证据使用。更重要的,首先还是解决“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这个主要依据问题,其次“松雪斋”的地理位置才有锦上添花的辅助作用,不可本末倒置,将这样的细枝末节作为出发点。
2、赵孟頫晚年大量书写小楷
赵孟頫的存世晚年小楷作品计有:延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跋《快雪时晴帖》、延祐六年八月五日书《洛神赋》、延祐七年正月廿七日为中峰和尚写《圆觉经》真迹摹刻刊印本。前者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后两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前者字不过百,中者字不过千,后者字数一万四。
并且,赵孟頫晚年写《圆觉经》不止一次。书信中,延祐六年有三条:七月二十三日致中峰和尚《还山帖》:“《圆觉经》尚有三章未写毕,一得断手,便当寄上。又恐字画拙恶,不堪入板”,可见摹刻刊印本也不止一种;八月十七日致中峰和尚《圆觉经帖》:“昨作书,以《圆觉经》拜纳,当已得达”;约十月,致中峰和尚《两书帖》有:“《圆觉》俟再写纳,并乞清照”。前后两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间一件为上海博物馆藏。
“松雪翁年老不复为人作小楷书”,更可能是官位日高,不为常人作书。这里的“人”翻译过来应为“常人”,有面子的皇帝、中峰和尚、亲家、自家,自然不是“常人”,提笔就写,并不含糊,怎么可以把一个学生的话当成数理逻辑一样绝对化理解呢。
同样,也不能根据赵孟頫晚年大量书写小楷反过来说杨载书法不对,作为学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是很正常的,正确的途径仍然是前面讲的图像逻辑。
3、古人小楷日书写量的常规与底线
关于每日书写字数的问题,不能以不怎么写毛笔字的今天人写小楷慢,刻舟求剑地想象古人写小楷也慢。小楷是古人日常最常用字体,记事、写作、抄经、应试等等都是用小楷。为什么要用小楷,因为小楷笔画尺度小起止转折轻动作幅度小、毛笔蓄墨量大不需经常蘸墨、字径小不用经常换纸、编纂成册信息量大,而且正常书写者并非作意临摹而是写的我体字,这就好比我们用钢笔记笔记,书写自然快。
以文献记载,如《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载,宋崇宁二年五月四日礼、户部奏议:“校书省见誊写三馆书籍充秘阁书……每月各人支钱三贯五百文,每日写字二千五百”。按每天有效时间6小时计,60×60×6÷2500=8.64秒/字,1分钟不到7个字,这么慢的速度,当然是给钱写字应付目标考核的一个低限水平,标准必须保证最低水平写工能正常完成,这样的速度只值每天116文,程民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对比同时期劳动力成本后感叹书写工“竟不如当时体力劳动之价”。
很难想象抄书一天都写不了2500字,科举如何答卷,审讯如何笔录。存世档案中殿试卷并不少见,嘉庆以后格式:素页2开备写履历三代约100字,弥缝;正卷8开,每开12行,共96行,正卷有红线界直无横格,又不得点句钩股、添注涂改;因此,外给草本一本,尺寸与正卷同,有纵格和横格,以便从草本誊录正卷时用以蓑衣比格(抄一行撕一行),既可横排整齐,又可防止错漏。草本行24字,低2字写,空2字留作“策冒”“策尾”颂圣双抬用。实际每行22字,满卷一般7开零4行共88行,谓之“七开半”,即22×88=1936字左右(参考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以1904年末科状元刘春霖殿试策为例:素页履历85字,正卷刚好1950字,合计2035字,自晨及昏,不添灯烛,起草誊录共4070字。前者用行草书写更快而有斟酌改添迟缓,后者用馆阁工楷书写更慢而无斟酌改添,后者或略长于前者。若全天誊录夜添灯烛,不比横格的工楷写经格式,当略近或高于此数。
至于赵孟頫,被鲜于枢、班惟志、陶宗仪称“后之览者,岂知下笔神速如风雨耶”“运笔如飞”“日书万字”,用“岂知”表示不可思议,自又比一般人更快。如果心无旁骛,又不需蓑衣比格横排整齐,小楷一天5000字,应属正常。换成俞和的功力,所谓两天写5000字,恐怕也只是两个大半日而已。若两个整天,则是任何正常书写者都能干的正常事,谈不上“令观者叹为神技”,于证真、证伪皆无裨益。
4、《道德经》的作伪者是俞和
当然,这里研究赵孟頫的书写速度,并不是要说延祐三年款的《道德经》就是赵孟頫的真迹,这件小楷无论是书法还是印鉴都是毫无疑问的俞和作伪,笔者已有详细论证(参考中国艺术出版社2014年《第三届中国书坛兰亭论坛论文集》,拙文《伪赵孟頫书画印考辨以俞和作伪赵孟頫书画为例》)。从书写水平上说,俞和较之赵孟頫虽有差距,但与陆士仁的扁薄、燥露、琐碎相比,则是天壤之别(图10),接下来的第二部分还将具体比较。
图10 俞和作伪赵孟頫款《道德经》与陆士仁《四体千字文》对比
《过云楼藏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卷〉辨伪》(p120~128)之辨析
图11 赵孟頫 《草书千字文》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辨伪》用了洋洋洒洒2000多字对《草书千字文》作时空证伪:
1)、根据杨载《赵文敏公行状》记载,《辨伪》简述“赵孟頫、张伯淳等人应诏赴大都,时间是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十一月,且赵孟頫居被荐人中‘首选’”,所以“此二十余被荐之人应同时赴大都,不可能有先后时间的差距”;
2)、程钜夫诏访遗逸不止一人,如张伯淳一同被举荐,《元史·张伯淳传》:“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学教授”,所以“张伯淳在赴大都的同年,即在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间,已经被授予杭州路儒学教授,即回其家乡做一名学官去了”;
3)、若干事实如:世祖接见、参议至元钞法、发难刑部郎中、授官兵部郎中等,都表明赵孟頫从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到二十四年六月都在大都;
4)、所以《草书千字文》中“吾有京师之行,趣迎上道,时至元丙戌十二月也”和“次年三月,驰驿至崇德”(图11)的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同样由于大量使用孤证、道听途说和想象,以上每一条都不成立:
1、荐选成行有先后
原文“十一月”是举荐时间,不是成行时间。“赵孟頫居首选”与“此二十余被荐之人应同时赴大都”没有因果关系,参见陈得芝教授论文《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考》(载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论文集》)中相关考证,荐选二十余人并非一蹴而就,是随荐随行,先后到达大都的,甚至有并未到达大都,仅仅是“姓名上于朝”。比如凌时中,字德庸,即程钜夫此行所荐(《元史》卷一百七十二《程钜夫传》),《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有文献7笔,《松雪斋文集》卷六《送凌德庸赴淮东宪幕序》即叙述了二人“今年之春,相遇于都下,握手言笑,若有雅故”。凌时中虽为湖州人,但以建昌路(今江西南城)司狱被荐,从江西出发,显然没有绕道杭州与赵孟頫等人同行。又比如叶李,因为是元世祖点名“必致”,没有考察过程,至元二十三年最早出发,所以同一批被荐的张伯淳就未与叶李同行,有张伯淳为叶李所写送行诗《送叶亦愚》为证。
2、张伯淳由学官被荐授宪幕,时间是至元二十四年
孤证《元史·张伯淳传》,其史源是程钜夫为张伯淳所作墓志铭,原文是:
“至元二十三年,某以侍御史受诏,选士南方。未行,闻廷绅有言公贤者。既至杭,公为博士,时犹未识公,而旧识识公者人人言公,与所闻同也。暨识,而心察之,又同也,乃荐之。明年报命,有防问所荐有可相者乎,对曰:“惟上所试,以观其材耳”,由是公晋居宪幙。”([元]程钜夫《雪楼集》卷十七《翰林侍讲学士张公墓志铭》)
“既至杭,公为博士”,诏访以前,张伯淳已经是学官;
与叶李不同,对张伯淳有一个由听说到“而心察之”的考察过程;
“明年报命”,程钜夫复命是至元二十四(1287)年;
“有防问所荐有可相者乎……由是公晋居宪幙”,张伯淳被荐授的官职是“宪幕”,即浙东道按察司知事,不是学官;
这个荐授官位虽低,却是用以试相才的,所以后来才有“在官二年,五祈闲不遂”,不许辞。为什么要五次请辞呢?墓志又言,大德六年(1302)夏,张伯淳“病终于官,得年六十有一……夫人赵氏前十三年卒”,因为张伯淳的夫人,也就是赵孟頫的五姐赵孟艮身体状况不佳,卒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按察司最后才不得不在张伯淳“在官二年”后批准请辞,由此倒推,也正是至元二十四年开始“晋居宪幙”。
《元史·张伯淳传》的记叙比《元史·邓文原传》好在并没有错误,只是过于简略,错误史料导致错误结论,简略的正确史料遇到随意的错误解读同样导致错误结论。
3、赵孟頫到达大都的季节有明确记载
赵孟頫初至大都写了一首诗《初至都下即事》:“海上春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不仅是春天,而且还是春深,柳色已经很浓了,显然不是什么冰封河冻的十一月。
这既与程钜夫“明年报命”一致,也是“明年报命”的原因。如吴澄大德六年十月底的一次由大都南还行程就因为“河冻不可行”,推迟到“七年癸卯春,治归,五月己酉至扬州”(吴澄《吴文正集》附录,危素编《草庐年谱》),非军情要务,程钜夫、赵孟頫、张伯淳不可能冒着封冻在半途的危险十一月出行北上。
4、赵孟頫的具体行程
《辨伪》对于《草书千字文》的释文有两处错别字,一处是“趣迎上道”应为“趣迫上道”,另一处是“次年三月”应为“次年三日”。按省略语法,次年三日,即次年正月三日。后一处错认甚至被《辨伪》专门用红线标注过,作为全文最重要的立论起点,实在是不应该。
按至大三年《兰亭十三跋》(图12)行程,最早时间款是“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于舟中”,地址是南浔北,日本静嘉堂文库藏赵孟頫致中峰和尚六帖册中《长儿长往帖》(图13)记载:“去岁九月离吴兴,十月十九日到大都”,将途经点南浔北,按水系恢复至德清,加2天,行程46天。
《松雪斋文集》卷九《大元封赠吴兴郡公赵公碑》:“五月十三日,孟頫被旨许过家上冢”,致中峰和尚六札册《得旨暂还帖》:“四月间得旨暂还……五月间离都,触暑远涉……六月廿日到家”,行程47天。
图12 赵孟頫 兰亭十三跋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13 赵孟頫 长儿长往帖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至元二十四年(1287)正月三日过崇德,按水系为杭州出发,时间为正月初一,以46天计算,到达时间应为二月十六日,对应格里高利历3月8日,通过天文历算,得1287年3月5日16时54分5秒“惊蛰”,正好“海上春深柳色浓”。
多重史源的反复校核下,偏信孤证的时空证伪至此全面崩溃。
《赵孟頫〈行书千字文〉辨伪》(P110~119)辨析
《辨伪》观察到该卷《行书千字文》(图14)中的“玄”“郎”二字缺笔避讳现象,认为是“难以解释的现象”,并展开了一个递进证伪思路:
图14 赵孟頫 行书千字文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此卷应是临写隋智永《千字文》的宋刻本,才会有避宋代皇帝名讳的现象”;
2)此卷“应是临写宋政和年间以后的刻本”。理由是撰写者行“敕员外散骑侍郎”改“梁员外散骑侍郎”应在政和年间以后,而赵孟頫的《千字文》写本均为后者;
3)“假如要如实临写,则不仅是上述二字避讳,还应避宋徽宗赵佶及此前的几代皇帝的名讳”;
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频《二体千字文》一册,同样书“梁”而不书“敕”,《千字文》无一字避讳”;
5)“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真草千字文》“玄”字避讳”;
6)“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赵氏《杜甫秋兴诗卷》书‘匡衡抗疏功名薄’一句中‘匡’字缺笔,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该诗卷首句‘玉露凋伤枫树林’中‘树’字,细察该字结构,其实也属缺笔字,应避宋英宗赵曙的嫌名讳”。考“此卷应是赵氏三十岁左右的早年所书,其时尚未应诏仕元。”
结论:“这说明,赵氏书法作品中避讳,应该有出仕前后的区别”;推论:“也就是说,若其仕元之后,仍在书写文字中有避讳现象,则提醒我们要注意了”;言下之意:有“玄”字缺末点“避讳”现象的《行书千字文》以及上博藏《二体千字文》都不对。
图15 赵孟頫书法真迹《行书千字文》《二体千字文》中的“被避讳”现象,“玄”字末点系藏家用工具刮去
首先是现象观察与描述,《辨伪》观察到的《行书千字文》《二体千字文》中的所谓“玄”字“避讳”,其实是后来的藏家用工具刮去的(图15),赵孟頫并没有避“玄”讳,而只是“被避讳”,赵孟頫能管住、或管不住自己,但肯定管不住后代藏家怎么想。
“郎”是正常书写,并没有缺笔避讳问题,“朗”字“良”旁缺末点,不能算正常的避讳,在赵孟頫书法中亦非孤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为张渊书《洛神赋》中“丹唇外朗,皓齿内鲜”的“朗”字就是相同写法。
现象描述已经错了,后面的推理本就毫无意义了,但相关推论的举证和论证方法实在匪夷所思,也很容易澄清:
1、《行书千字文》并非临摹自智永《真草千字文》宋刻本
此卷《行书千字文》临摹自智永,是个未经证明的立论,但却很容易证伪。比如所有版本智永《真草千字文》均作“律召调阳”,而所有赵孟頫写本均作“律吕调阳”,书写方法差异也很大(如图16)。这样的文字问题只不过是蒙学记忆或元代书肆刊印本的版本问题而已。“敕员外”与“梁员外”问题也正说明此卷《行书千字文》并非临摹自智永《真草千字文》宋刻本。
2、赵孟頫书法中的避讳与不避讳现象
《杜甫秋兴诗卷》中“匡”字有避讳现象,缺末横。“树”字是正常书写,没有避讳问题,可参考《闲居赋》《秋声赋》《远游》《天冠山诗(延祐二年本)》等;
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所藏三本赵孟頫《千字文》真迹写本,《乐善堂帖》刻本中赵孟頫行书《千字文》等,所有“匡”字缺顶横避讳(图16),而其他宋朝皇帝讳不避;
图16 关中本智永《真草千字文》与赵孟頫书千字文用字及避讳或不避讳字例
赵孟頫书法与文章中,有避讳现象和不避讳现象的还有:
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小楷《褉帖源流小楷卷》真迹,避“永”字家讳,缺末笔(图17);
2)美国弗瑞尔美术馆藏,小楷《常清静经》真迹,避“永”字家讳,缺末笔;“玄”字被刮去末点,又被补墨;
3)临《兰亭序》以及大量抄录书法作品中并不避“永”字家讳(图17);
图17 赵孟頫书法真迹中的避讳与不避讳现象
(左,北京故宫《临兰亭序》;右,台北故宫《褉帖源流小楷卷》)
4)作文避讳比抄录古诗文容易,汉语里有丰富的同义词,避讳可以自由遣词而无需缺笔,《松雪斋文集》中,并无刻意避宋讳家讳问题。但也有一些不合理低频字,如“玄”字0次、“匡”字1次,“玄”“匡”都是常用字,不合理的低频不排除有避用因素,但“匡”字的使用说明并不刻意;“永”字虽有16次,但基本都是地理、人物名词以及引用、奉敕制文等;父讳“訔”字3次,都是与祭父有关的文章,一般是留空格由他人填讳,但“訔”既是避讳字也是生僻字,本就不会出现在一般诗文中。
3、伪赵孟頫书法及作伪者、嫌疑人的本款书避讳情况:
1)俞和作伪赵孟頫款《四体千字文》“匡”字缺顶横避讳;
2)俞和作伪赵孟頫款《六体千字文》“匡”字不避讳;
3)俞和本款《篆隶千字文》“匡”字不避讳;
4)陆士仁本款《四体千字文》“匡”字均不缺笔避讳。
这些,都只是现象,有一定规律,但没有必然或必不。赵孟頫不避讳“玄”字,没有问题,要避讳“玄”字,也没问题,避不避讳最没有关系的就是仕元与否。《赵孟頫〈行书千字文〉辨伪》无论是现象观察、证伪过程、结论、推论都是错误的。
4、薛定谔的猫——避讳现象与书画鉴定
用避不避讳来鉴定书画,以前有过一些貌似成功的案例,后来大多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实际案例中,法律理解误差、执法不严格、书写不守法等问题普遍存在。而历史上因不避讳而被执法的其实都不仅仅因为不避讳,避讳问题历来就是一个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的口袋罪,执法特征就是对人不对事。同时历史上也没有过强行禁止避讳,改朝换代,已不需避讳的字有人愿意避,没有人阻拦,也无从执法。民间书写,公开的就避、私下的就不避,想起来就避、没想起来就不避,想自定一个避讳就自定一个,规律性差,随意性强,有统计价值,却无个案价值,就像薛定谔的猫。
最生动的两个案例,一个是北宋大观三年(1109)薛嗣昌刻关中本《智永真草千字文》,避讳情况如图18、表1:
图18 宋拓关中本智永《真草千字文》中避讳与不避讳现象
表1 关中本《智永真草千字文》中避讳情况一览表
按“‘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庙而七。’除太祖为不祧之祖外,大抵七世以内则讳之,七世以上则亲尽,迁其主于祧,而致新主于庙,其已祧者则不讳也”(陈垣《史讳举例》第四十五《已祧不讳例》),宋徽宗排第八世,宋钦宗排第九世,宋高宗排第十世,但是实际上到绍兴三十二年才有“钦宗祔庙,翼祖当迁,以后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宋史》卷一〇八《礼志》中),宋孝宗以后“敬”字才以法律形式正式退出避讳。薛嗣昌这里楷书连犯“敬”“殷”“恒”三讳,草书有“玄”“让”两讳例,说明草书从技术上说是可以避讳的,而应讳未讳有八处,尤其是“匡”字为不祧之讳而未避,实在是无人执法、有法不依、法不责众。
另一例,无论是翼祖之讳“敬”字,还是宣祖之讳“殷”字,米芾都比薛嗣昌解讳得早。如《竹前槐后诗帖》《致伯充帖》《贺铸帖》《李太师帖》之“敬”字不缺不讳;《蜀素帖》中两个“殷”字,一个避讳缺末笔,一个不避不缺笔(图19)。私密空间、法外之地,被选择性执法的风险不敌一幅蜀素的价格,但写到末尾想起来要避讳也没有必不的固执。拿必然或必不去规定赵孟頫又有什么道理呢?
图19 米芾《蜀素帖》中的两处“殷”字
附录,近年来避讳证伪失败案例举略:
1、张旭《草书四帖》“北阙临丹水”,猜测原诗应为“玄水”,而“玄”字犯宋讳,故改“丹”字以避之。实际原诗地理背景确有丹水地名,“玄水”的猜测是错误的。
2、颜真卿《颜勤礼碑》中“世”字无缺笔,犯李世民讳。实际唐代有专诏“世民”二字不连用可不避,颜真卿对于“世”字有时避有时不避,大多数时候不避。
3、赵佶《楷书千字文》犯宋讳而避清讳。实际避宋讳而犯清讳。
4、苏轼《功甫帖》“议”字犯赵光义嫌名讳。实际上宋代有专诏“光义”二字不连用不讳,大量实物“光”字“义”字均正常书写。
《辨伪》的鉴定过程充满主观感受缺少图像分析
《辨伪》全书将主要笔墨集中于貌似“破绽”“硬伤”的考察上,而风格辨伪往往寥寥数语,如《赵孟頫〈六体千字文〉再考》(p50~58):
1、列举对照品:“将《六体千字文》一卷与陆士仁《四体千字文》逐体比较”;
2、比较结果:“除个别文字的结构、形态有些变化外,大都不仅‘确有相似之处’,且很多文字书写‘更似模子刻印一般无二’”;
3、作图:“如将四体剪裁成每体一行,排成《六体千字文》的形态,然后加以比较”(图20左、中);
4、比较结果:“就更能一目了然了”;
5、再将俞和《篆隶千字文册》也如法炮制(图20右):“同样一般无二”。
结论:赵孟頫款《六体千字文》、俞和《篆隶千字文册》都是陆士仁作伪。
图20 陆士仁《四体千字文》(左)、赵孟頫款《六体千字文》(中)、俞和《篆隶千字文册》(右)对比
从简单例图剪贴直接跳到结论“确有相似之处”“更似模子刻印一般无二”“一目了然”“同样一般无二”,所有这些文字都只是个人“主观”感受,完全没有具体特征描述、比较、排他的过程。如果排除作者身份,作“感受”检验,这样的感受很难达到“主观”“客”也能“观”的共鸣。
中国汉字,尤其是楷书、篆书、隶书这些偏静态的书体,本身具有稳定的结构、笔顺,书法的传承,又有学习临摹过程,两件题材类似作品之间比较,大概率会得出某些方面“确有相似之处”的结论。
从逻辑上说,“相似”是相互的,如果A相似于B,那么B相似于A;“相似”又是传递的,如果A相似于B,B又相似于C,那么C相似于A。凡是陆士仁学习过的人,或有学习渊源的人,反过来都有某些不太重要的汉字基本共性像陆士仁。这种相似,换成“李士仁”“张士仁”“王士仁”,也会有很多人得出“确有相似之处”甚至“同样一般无二”的主观感受。按照这个思路,整个明代及以前书法史都可以被臆想成陆士仁伪造。
个人主观感受描述式的鉴定方法,在过去鉴定任务繁重的时候,以信用背书的办法,或可权宜,如果结论能经得起检验、做得到预见,也不必苛求。但以论文形式对已产生的重大共识轻言可否,主观感受鉴定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认识论条件下,人们对于鉴定的科学性要求,这就需要一些鉴定原则。
鉴定的一般原则
以图像比较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古书画鉴定,要讲究科学性,我认为应有以下原则:
1、鉴定要有正确的真伪观
每个书画家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审美观点不同、习惯不同、工具不同、技术水平和能力不同,必然形成特有的风格。
这种特有风格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变化性、统一性,区别于其他人,从而可以“识真”;模仿者、作伪者可能在少数局部上形似被作伪者,同样会在多数局部有其个人特有的风格,区别于被作伪对象,从而可以“辨伪”。这是“主要依据”的依据,是必然性的。
之所以存在鉴定困难,是因为我们个人对这种稳定、连续、变化、统一、区别的特征缺乏认识,主要是我们的主观原因,不能怪作伪者水平“太高”。
我们暂时没有认识到的这些特征,称之为“隐秘特征”,鉴定工作正是要把这种“隐秘”揭示为“显著”,而不是制造不可知论。
那么,要鉴定赵孟頫、俞和、陆士仁书法,三个人的真迹分别有哪些,各自排他性特征是什么,待鉴作品与真迹的具体联系与差别是什么,都需要解答,如果解答不了,不妨暂时停下来。《辨伪》只简单列举了一件陆士仁真迹,未作任何分析,也未列赵孟頫和俞和标准品,这显然是不够的,不能“识真”如何辨伪。
先列举出来的标准品、参考品,如果标准品本身就有问题怎么办?列举,可以视为一个假说体系,如果不断被检验,那么假说就成立,检验中出现矛盾,那么假说需要修订或不成立,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学术渐进,靠的是有质之疑而不是猜疑,靠站得住脚的证据与逻辑,数学、自然科学中的很多经典定理就是这么得来的。
2、特征必须是可准确描述的
既然我们能够发现和认识显著特征甚至隐秘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具有排他性,那就一定能用鉴定语言而不是个人感受描述,准确描述特征是鉴定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现代鉴定,就是要将存在于眼学主观中的书画鉴定,客观地描述出来,介绍给读者。
比如,汪珂玉《珊瑚网》卷十收录的明桑悦《俞紫芝楷书悟真》有评:“紫芝(即俞和)所书,深得松雪(即赵孟頫)笔意,而圭角稍露,比之松雪正如献之之于羲之也”,这里的“圭角稍露”就是一个准确描述,而“深得松雪笔意”,桑悦也有把俞和作伪作品当成“标准品”的嫌疑。如果说俞和楷书“深得欧阳询笔意”,那么俞和作伪赵孟頫楷书可以很容易从“标准品”中跳出来。
描述并不局限于语言文字,还可以用图像、辅助线等标注,新媒体甚至可以用动画等办法进一步解析,“难说与君画与君”。
例如笔者对赵孟頫、俞和、欧阳询“之”字横撇转折中“圭角”情况的的图像标注(表2),俞和特有的B坡学自欧阳询,迥异于几乎没有B坡“松雪笔意”,这其实是一个圭角多少、有无的简单定性统计问题。进一步的,可以对BC坡的长度比进行定量统计,都是准确描述的方法。
表2 俞和与赵孟頫小楷书法中“之”字圭角比较
注:本表为赵孟頫、俞和众多显著性差异中的一种,更多特征比较参考拙文《伪赵孟頫书画印考辨——以俞和作伪赵孟頫书画为例》
过去,赵孟頫真印和俞和伪印一直被忽视,没有被统计和准确描述,造成标准混乱,通过矢量图软件辅助标注(图21),今天一般人都能轻易目见其巨大差异,准确区分:
图21过去被忽视的赵孟頫真印(上)与俞和作伪印(下)存在巨大的差别(赵孟頫印、松雪斋、大雅、天水郡图书印等真伪差别同样巨大,这里略举其一,仍见表2注释)
比如,“昂”字(印面左下)左部两脚,用正圆弧曲线拟合显示的曲率和半径差别就非常明显,赵孟頫真印曲率大、半径小,B圆心在框内,俞和伪印曲率小、半径大,B圆心在框外;
同样是“昂”字右部S形曲线“1”号缺口,位置差距大于1毫米以上,赵孟頫真印在下行弯道转横向直道相接处,俞和伪印则在横向直道末段转下行弯道前;“昂”字下方“8”号缺口是俞和伪印所特有;等等,其他局部也都可以准确描述。
这些由隐秘而至显著的区别性特征,并非单个印蜕、单个局部的偶然钤盖误差,而是印面全局更多位置、经过数十件作品全面统计得出的必然差异。
《辨伪》中只有个人感受,没有任何具体描述,让读者如何知道作者找到了或显著或隐秘的排他性特征。
3、描述及结论应有可重现性
简单地说,“可重现性”即“客观性”。
如果不同人在不同时刻、不同地点,以同样的前提和同样的规则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即称该结论具备可重现性。
隐秘特征一旦被揭露即为显著特征,无论是甲来描述、乙来作图、还是丙来统计,赵孟頫和俞和的圭角差别、印鉴差别等等都是显著的,都可以得到同样的比较结论。
由主观及客观,主能观的客也能观,这种可重现性是科学的基本属性之一,也是准确描述的目的。主观而客不能观的个人感受,如“确有相似之处”“更似模子刻印一般无二”“一目了然”“同样一般无二”,在非诱导的情况下,很难做到重现性。
4、图像鉴定应保持独立性,鉴定结论应具有预见性:
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的认识高低,是鉴定水平和能力的体现。鉴定者,应该有局限于作品本身风格分析,不依靠任何辅助依据,独立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
预见性是指从现实事物的发展规律中把握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古书画鉴定中,特征与特征的组合,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通过已知局部的A特征,可判断未知局部中的B特征,并获得解密检验,这就是古书画鉴定中的预见性。
预见性并不以主观感受结论的发表为特征,而是以能否获得检验为特征。
熟悉的案例如“徐半尺”雅号的来历。一次,有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于是徐邦达得名“徐半尺”。
徐邦达的鉴定信心正是来自于对“主要依据”的掌握,在没有任何辅助依据的情况下,敢于根据局部图像独立作出全局结论,最后被检验,这就是预见性。
预见性、可检验性是任何鉴定者必备的素质,也是鉴定信用的最大加分项。
书画家与作伪者的差别,一定是众多显著特征的组合构成的,亦可参见笔者论文(如表2注释),通过少数特征判断得出的结论,可以被其他特征检验,当然也可以被辅助依据检验。例如台北私人藏赵孟頫款《四体千字文》:
1)早期公开图像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图22);
2)根据图22中“深得欧阳询笔意”而区别于赵孟頫的风格信息,可判定为俞和作伪,这个结论2014年发表在第三届中国书坛兰亭论坛的论文中(图23),并推测其未公开印鉴亦应为前文图21中的俞和作伪印;
3)到2017年12月,故宫出版社《赵孟頫书画全集》第十册首次完整出版(图24),各种书写特征清晰无误,所有印鉴第一次公开,完全符合俞和特征,检验了上述预见。
图22《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附图赵孟頫款《四体千字文》局部
图23 拙文2014年预判赵孟頫款《四体千字文》待定印章“应为俞和伪印”
图24 清晰图像证实赵孟頫款《四体千字文》确为俞和伪印
又如,金琮、詹僖、黄彪、章藻等历史上最优秀的赵孟頫书画作伪者和最大受益人,各自都有稳定的书写特征,稳定地使用自制的同一套特征明显、差异显著的伪印(图25),亦可在鉴定实践中设盲检验。
图25 真伪赵孟頫书法与各具特色的真伪印鉴对应关系设盲检验
《辨伪》一书,从似是而非的辅助依据出发,缺少对作品本体特征、差别的准确描述,做不到客观,展示不出预见性,让人如何信服。
俞和与陆士仁书法的鉴定问题
那么俞和作伪赵孟頫款《六体千字文》、俞和本款《篆隶千字文》,与陆士仁《四体千字文》是不是“确有相似之处”“更似模子刻印一般无二”“一目了然”“同样一般无二”呢?
当然不是。不仅不是,而且差别显著,文字描述、图像指示都能非常简单明确地显示,二者在艺术追求和书写水平上有着巨大的差距。
表3 赵孟頫款《六体千字文》俞和本款《篆隶千字文》陆士仁本款《四体千字文》比较
表3的这些图片比较只是极少数字例和极少数特征的比较示意,又如中锋、折笔、钩笔、蚕头、燕尾、笔画组合、穿插、空白、布局等,陆士仁《四体千字文》,书写基本功尚且欠缺,与《六体千字文》《篆隶千字文》二者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望尘莫及的。
这里所谈,仅仅是《六体千字文》一篇的问题,赵孟頫《行书千字文》《二体千字文》《草书千字文》真迹、俞和作伪赵孟頫款《小楷道德经》《九歌书画册》、俞和本款《篆隶千字文》、邓文原章草《急就章》真迹等都被《辨伪》判为陆士仁作伪,以及《自写小像》被判伪,绝大多数题跋书法的鉴定,同样缺少深入的图像分析,大都是错判。
余论
现代鉴定,需要更加深入的图像分析、更加客观的描述技术、更加严密的逻辑阐述,文史考证首先应对史料进行辨伪,即使是正确史料的使用,也应注意多源互校、正确解读,廓清时间、地点、人物,了明起因、经过、结果。
以上限于篇幅,仅就《辨伪》中赵孟頫及相关部分的核心论证以及相关原则略作展开,实在是挂一漏万。《辨伪》一书,主要依据论证粗疏,文史考证大量使用孤证途说,更多问题,尚有待读者去解决。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微信 美文-微信文章库-我的知识库 » 赵华:辨伪,怎能如此简单粗暴?读肖燕翼《古书画名家名作辨伪三十例》